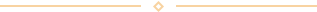加快地方债发行并不能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困境
来源: 2018-10-11 分享:
知名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困境根本原因来自财政体制,因此,化解地方债风险需要从财政体制改革上多方面着手,包括减少地方政府债务事权、合理匹配地方政府事权和财力等。
该分析师指出,地方政府债务是特定财政体制下,政府收支结构形成的结果。政府债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财政收不抵支,需要融资,形成政府债务;另一方面,政府进行投资形成资产,同时借助杠杆融资,形成债务。而地方政府收入来自本级财政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因而本级财政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如果不能覆盖地方政府支出,则会形成债务。
“而地方政府支出则又由地方政府事权决定,收入则由地方政府财权和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决定。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结构以及中央转移支付力度是决定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原因。”该分析师在报告中称。
该报告援引数据指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不久,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就进入持续上升通道。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11.1%持续攀升至2007年的18.4%。金融危机后继续攀升,2017年达到24.6%。
该分析师表示,相较于1996年水平,政府支出占GDP比例翻了不止一番。而广义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攀升更为明显,从2008年的27.1%大幅提升至2017年的38.0%,增加10.9个百分点。政府支出占GDP比例的显著上升显示政府事权明显扩大。
在该分析师看来,针对地方政府债务本身去治理往往是治标之策,因为在没有改变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制的情况下,仅仅针对地方政府债务本身去治理,收效往往有限。而且,由于会受到其它条件的约束,例如受经济稳定增长的约束。
比如,金融危机以来,对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就呈现出明显的周期特征,政府债务周期与经济周期互为因果。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稳增长政策占上风,因而对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往往放松,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推升经济增长。2009年、2012年、2015-16年都出现过这种情况。随着经济企稳回升,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乱象加大系统性风险,因而防风险占据主导位置,对地方政府管控显著加强。2010-11年、2014年以及2017年至今都是政府债务管控强化期。而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强化则往往导致基建投资增速下跌,加剧经济放缓压力,使得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因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恶性循环。
此外,该分析师认为,加大地方政府债发行并不能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困境。他指出,今年1.35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仅占当年基建投资的7%左右,难以有效满足表外融资、城投融资收缩留下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债发行的规模节奏决策权不在地方政府,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更无发债权,更难以借助地方政府债来弥补资金缺口。
该分析师表示,“拆弹”地方债风险需要从财政体制改革着手。
首先,减少地方政府债务事权,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事权过大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过重的根本原因,大事权决定大的支出责任,而支出过大,则意味着债务负担不会轻,减税也比较困难。
其次,合理匹配地方政府事权和财力,缩减地方政府资金缺口。在减少地方政府事权,减少支出责任的同时,需要增加地方政府财力,以缩减地方政府资金缺口。一方面,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引入房产税或物业税体系,将其收入归于地方,补充地方政府财力。
他同时表示,政府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政府事权需要缩减,但政府支出责任的减少需要对应民间支出责任的增加,否则会出现经济活动显著的收缩。在非政府经济进入原有政府建设领域需要时间的情况下,政府事权的缩减不可操之过急,需要循序渐进,以保障经济稳定。
国投观点
政信投资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如何能够化解地方债,需要的是各方携手努力,调控手段要顺应经济学规律,而不是草率干预。首先要认清资本有逐利的本性这一点,从“利”上下功夫而不是从“资本”上下功夫,要寻找新的利益增长点,摆脱楼市泥沼,挖掘实体经济潜力,培养实体经济长足发展的经济环境。其次要制定利好于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行业政策,加大对高精尖领域的扶持力度,开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实体经济就具备了“造血”功能,资本自然会从虚拟端流向实体端,从而实现金融和经济共荣共生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
另外,债务高企的地方政府也应自省,在大搞建设之前要重点做好项目前期立项论证和投资方案设计,避免为了政绩而不够后果地借钱开发。政信投资集团以政信金融服务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的同时,也帮助健全政府信用体系建设和破解融资难题。“政信投资集团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可以提供项目全方位服务,从立项到落地过程中,不仅重视投、融、建环节,更将‘管’融入项目可行性研究中,注重项目后期运营和管理,确保项目实现创收,真正做到合作共赢”。